作為著名的 Rotterdam 唱片公司、唱片行和發行商 Clone 的創辦人,同時擁有超過 30 年的 DJ 經驗的 Serge Verschuur(通常稱為 Serge)對音樂的實質性有著細緻的理解;對舞池上錯綜複雜的心靈-身體動態有所了解。
他表示:“物理過程比人們想像的更重要。它給你能量,讓你想要移動,讓你想要創造。這就是好的舞曲所做的,也是我仍然被它吸引的原因。”
Serge 對舞曲的愛,起源於當地的廣播節目,和 80 年代夜店的煙霧瀰漫。
從燈光技師和臨時 DJ 的工作,到在每次下班時清理煙灰缸的工作,俱樂部環境中的每個環節,Serge 都非常沉浸,他被一種對於聽音樂和分享音樂的渴望所支撐著。
“我只是在尋找可以播放我喜歡的唱片的地方,”他回憶道。他在 17 歲時朝聖阿姆斯特丹的 Roxy Club ,那裡他第一次接觸到 house 和底特律電子音樂。
在 90 年代初,Serge 成為荷蘭西海岸的固定班底,在海牙舉行了一系列著名的通宵和 Acid Planet 派對。
1992 年,他以 Orx 的名義發行了首張 EP《Coördinated Sounds & Sequences》,並創立了唱片公司 Clone Records 。
Clone 以電子音樂、house 音樂和 techno 為基礎,在那之後已經發行了來自 Aleksi Perälä 、Legowelt 、Randomer 和 Roman Flügel 等藝術家的音樂。
通過對 Drexciya 、The Other People Place 和 Der Zyklus 等樂手的唱片的重製,Clone 進一步鞏固了底特律和鹿特丹音樂場景之間的連結。在 Clone Records 旗下還有一些子廠牌,包括以科技為主的 Basement Series 、以 house 為中心的 Royal Oak ,以及致力於芝加哥 house 的 Clone Jack for Daze 。
三年後,Serge 在 Clone 旗下成立了一家唱片店和發行部門,專門經營來自不同國際唱片公司的電子音樂、原聲音樂、爵士、Funk 和義大利disco 。
如今,Serge 繼續擔任 DJ ,同時經營 Clone 的所有方面,充滿對分享音樂的堅定和熱情。
在 Carhartt WIP Radio 的這一集中,Serge 通過一個充滿能量的混音,向大家展示了 Clone 最近目錄中的曲目,同時向底特律致敬,因為那是 techno 的發源地。
一如既往,混音伴隨著一場深入的訪談,Serge 在訪談中探討了 Clone 名字背後的哲學,以及唱片公司對於現在的重要性,同時使用一個引人入勝的橡樹的來比喻音樂行業。

-你對電子音樂的熱愛是什麼時候開始的?
Serge: 我對電子音樂的熱愛始於收音機──讓我聽到那些充滿魔力的曲子。
最初是透過荷蘭廣播台的 Soul Show 開始的,會在每週四晚上播放,其中有一個 Bond Van Doorstarters 混音,展示了我以前從未聽過的曲目,那時我還太年輕,無法去夜店。
當時有義大利 disco 、freestyle 、high-energy disco 、electro 和 R&B 。
有 The Flirts 、Mantronix 、Man Parrish 、Jonzun Crew 、Bobby Orland o、The S.O.S. Band 、Five Star 等藝術家的曲目。
然後開始出現第一批 house 和 techno 唱片,我聽到許多令人驚艷的音樂。
許多當地的夜店也開始播放所有的 house 和 techno 進口唱片,以及新的熱門 beat 曲目。
-在 90 年代,全職 DJ 的工作並不像現在這麼受歡迎。你是如何進入這個行業的?
Serge: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一名 DJ 。
我只是喜歡音樂,想聽到我喜歡的曲子,並與舞池裡的人分享。
購買唱片是擁有好音樂的唯一途徑,所以我慢慢開始收集。
大約在 1988 年,我認識了一位來自當地夜店的 DJ ,他有一張 Armando 的《100% Disin' You》的拷貝唱片──我總是拜託他播放這首歌,因為我自己沒有這張唱片。
然後我開始帶自己的唱片到夜店,問他是否也能從中選一些來播放,他答應了。
我想在某個時間點,夜店的人開始對我感到厭煩,在一個寧靜的星期五晚上他說:“你自己選喜歡的播吧。”那應該是在 1989 年。從那時起,我開始在 DJ 台附近晃蕩,幫忙負責燈光。我還成為一位備用 DJ ,直到能夠在原本的 DJ 休假時,自己完成表演為止。
那家夜店位於當時著名的度假勝地 Renesse 。
那個小鎮就像是荷蘭版的 Rimini ,鎮上大約有六七家夜店,夏季每天都營業,那對我而言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環境。
我想那時候我才算是真正成為 DJ ,但這是一份糟糕的工作。
我可能得到的薪水大約是每個班次 40 荷蘭盾(約 18 歐元),是夜店中最低的工資,我每晚還得清理所有煙灰缸。
透過這個工作,我成功地與鹿特丹和海牙周圍的其他人和場地建立了連結。
我從來沒有把 DJ 視為一份工作或職業的轉變。
1991 年,我在馬略卡島工作,夏季在三家酒店擔任 DJ 。
我用那些錢,與一位 DJ 和朋友一起投資了錄音室設備,這讓我們的層次往上跳了一階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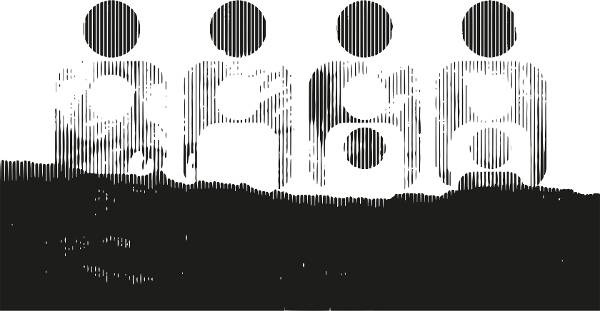
-你以《Coördinated Sounds & Sequences》這張 EP 推出了 Clone Records 。是什麼促使了這次發行?在 Ableton 等程式問世之前,你是如何製作音樂的?
Serge: 一切主要都是模擬的,並在 Atari 電腦中進行設計。
自從 80 年代末以來,我就完全愛上了音樂領域中所有的新發展。
Techno一直都是關於新技術、新聲音、走向未來、網際網路,使用任何能夠為音樂注入新能量的新設備。
在風格上,芝加哥和底特律的唱片公司對我來說是巨大的靈感來源。
自 1988 年以來,techno 和 acid house 開始變得更加抽象,因此那種抽象和現代主義的風格也啟發了我。
例如,像 Armando 、Model 500 、Blake Baxter 、Mr. Fingers / Alleviated Records 、Jeff Mills 、Robert Hood 、Underground Resistance 和 Richie Hawtin 這樣的藝術家。
還有荷蘭的製作人,如 Speedy J 、Eevolute Records ,或者像 Transmat Records 和 Planet E 這樣的唱片公司。
我想要以極簡和抽象的方式,進行製作和實驗,獨立地創作新的原創音樂。
這就是 Clone Records 的開始,受到所有這些獨立 DIY 唱片公司的啟發。
-你創立 Clone Records 的初衷是只發行自己的音樂,還是也想發行其他藝術家的唱片?
Serge: 最初的想法是創立一個唱片公司,讓我跟朋友可以發行我們自己製作的音樂。
開始時我並未將其視為一個商業計劃,我也沒有考慮過在那時發行其他人的唱片。
但在某個時候,我開了唱片店,遇到了很多製作出色、原創音樂的人。
此外,一旦店開張,郵購業務開始進行,我在工作室的時間變得極為有限。
因此,這間接的導致我開始發行其他人的音樂。這都是自然的發展與過程。
-唱片公司名稱背後的哲學是什麼?
Serge: 這是對所有啟發過我的唱片公司和藝術家的致敬,我“複製”了他們所做的。
這個概念是將一個小型 DIY 、地下唱片公司,視為對主流唱片公司的反文化運動,是一種獲得創造性自由的方式。
唱片公司作為一個創意的出口,使我們能夠在舞池上播放我們想聽的音樂,而無需受制於所有公司的廢話。
因此,這並不是什麼華而不實的東西,只是像許多其他人一樣,一個充滿熱情的計畫。而且,名稱也很簡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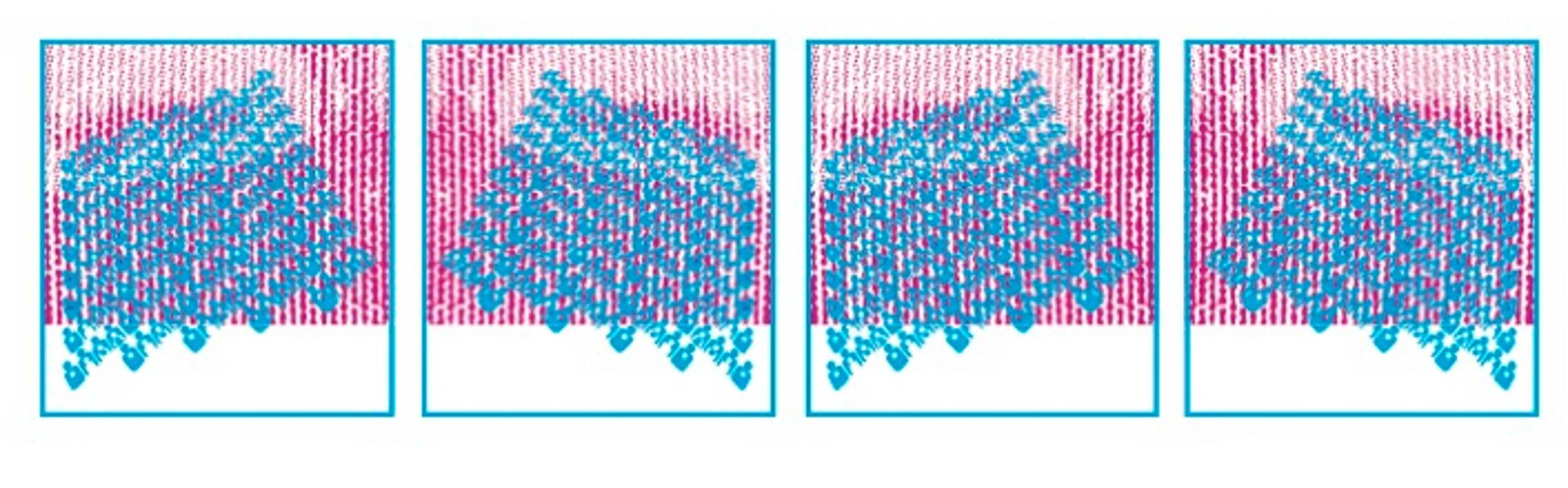
-如果你能用一句話描述 Clone universe 的音樂風格,你會怎麼說?
Serge: 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!
我會說我們扎根於電子音樂、house 和 techno 豐富的文化中,其中進行探索、加入個人特色和展現創造力,比在商業中取得好成績更重要。
而且呈現的方式,和獨特的音樂風格,比本地音樂的教條更重要。
風格應該要是很好辨識的!
-Clone Records 擁有豐富的音樂種類,包括了 Alden Tyrell 、Duplex 、Drexciya 、Legowelt 、Der Zyklus 、Dopplereffekt 和 Unit Moebius 等藝術家的作品。這些年來,你是如何建立這些聯繫的?
Serge: 世界很小。我在尋找唱片、合成器或鼓機的時候會遇到不同的人。
我會在派對上、在店裡,或者通過傳真跟他們互相聯繫,試圖購買唱片或僅僅表達欣賞之情。
當然,現在傳真已經被電子郵件和社交媒體所取代。
與志同道合的人建立聯繫是很容易的。
我們可以很容易的理解彼此,儘管說著不同的語言或來自不同的背景。
所有這些人都是我們構建網絡、傳播我們喜愛的音樂的原因。
Clone 的標誌上有四個角色,被稱為“家族標誌”,因此每位藝術家都是我們音樂家族的一部分。
-Clone 還會發行其他唱片公司的音樂。你如何描述你的發行種類的風格?
Serge: 我們很難歸納公司發行的種類,因為它是許多風格迥異的個體的總和。
在我們的分發名單中,一位藝術家或一個唱片公司擁有獨特或個人的風格,以及某種特有的音樂風格,這比擁有一本風格手冊或規則更重要,創造性的自由是最重要的。
發行商不應該充當某種守門員的角色。如果我們承諾合作,那麼每位合作夥伴都應該追隨自己的創造之路。
分發名單涵蓋了從 Larry Heard 的 Alleviated Records 到 DVS1 的 Hush 唱片公司,Donato Dozzy 的 Spazio Disponibile Records ,I-f 的Viewlexx Records ,David Vunk 的 Moustache Records ,Juan Atkins 的 Metroplex ,FJAAK 的 Spandau 20 label ,Jovonn 的 Body ’N Deep ,Detroit In Effect 的 M.A.P. Records ,以及 Cultivated Electronics 的電子音樂發行等。
Serge: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。是的,我認為會,但方式可能不同。
在音樂歷史上,愈早期的作曲家,通常主導地位越高。
但對我來說,Larry Heard 是一位音樂天才,可以與
Miles Davis 並列。
這就像是一棵巨大的樹──比方說,一棵皇家橡樹,樹幹越往下,就越重要。
在樹枝的末端有成千上萬的葉子,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來說,所有的葉子都是可以替換的。
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地下:根部和樹幹同樣重要,甚至可能更重要。
因此,找到那些在樹的根部和樹幹處的相似音樂,以及那些可以替換的葉子,這每個季節都在變化。
可以說,
Bach 和
Beethoven 正在不同的樹上生長,而 Miles Davis , Larry Heard , Drexciya , Legowelt , Donato Dozzy , and Juan Atkins 則屬於另一棵樹,對人們而言可能更像
Mozart 一樣重要。
對我來說,Larry Heard 是一位音樂天才,與 Miles Davis 並列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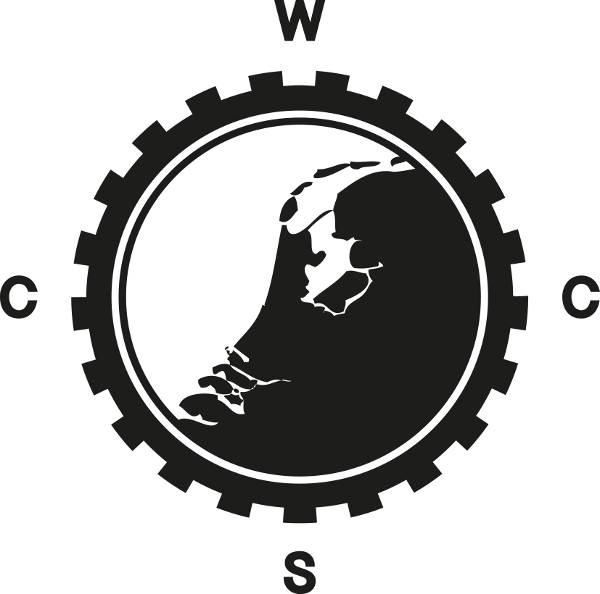
-你對於音樂在現代的價值有什麼看法?豐富的音樂透過什麼方式,改變了我們對音樂的感知?
Serge: 我認為在之前的問題中我也提到了這一點──在這個時代,每個季節樹上的葉子都在變化,並且變得可被替換、取代時,音樂的價值是多麼重要,相對於那些不可替換的音樂的價值。
Model 500 和 Cybotron 的音樂將永遠具有價值。
人們總是願意為這種音樂付費,即使只是把它當作一個可供擁有、從自己的唱機播放,或者擺放在書架上的收藏。
即使它在網路上可以免費獲得,人類天性使然,我們仍然想擁有一些有形的東西,收藏神聖的物品。
-舞曲的哪個部分,直到今天仍然吸引著你?
Serge: 我喜歡那種身體上的連結。
很多音樂都是用腦袋去體會的,但我喜歡去感受到來自肩膀下方的音樂。
我喜歡真實感受和體驗音樂,將身體和思想聯繫在一起。
它給你能量,讓你想要動起來,讓你想要創作。
但如果它僅僅是身體上的感受,而大腦沒有被某種獨特性或某種抽象形式所觸發,對我來說那就很無聊。
所以它需要同時對於腦袋和身體都能造成刺激。
-你目前還在持續擔任 DJ ,這些年以來,你是如何保持高度的熱情和能量的?
Serge: 你需要保持熱情!
每當我聽到一張刺激我的大腦和身體的唱片時,我就會得到能量,想要在夜店大聲播放。
-你如何保持對所有新發行的音樂的關注,以便為你的演出做好選擇?你仍然在演出前進行曲目選擇嗎?
Serge: 是的,這是我所做一切的核心。我總是在尋找新的和出色的曲子,甚至是老的音樂。
發覺一首歌並想與他人分享的感覺,這就是一切的意義!
-2024 年我們可以對於 Clone 以及發行有哪些期待? 有什麼新音樂正在籌備中嗎?
Serge: 總是會有新的音樂!Legowelt 有一張新專輯即將推出、DJ Sotofett 也將發行一張完整的專輯。
The Exaltics 已經準備好一張出色的新 EP 。Aleksi Perälä 將在黑膠上發行他的一些環境音樂的項目。
在 Clone Royal Oak 上也會有很多出色的 house 音樂發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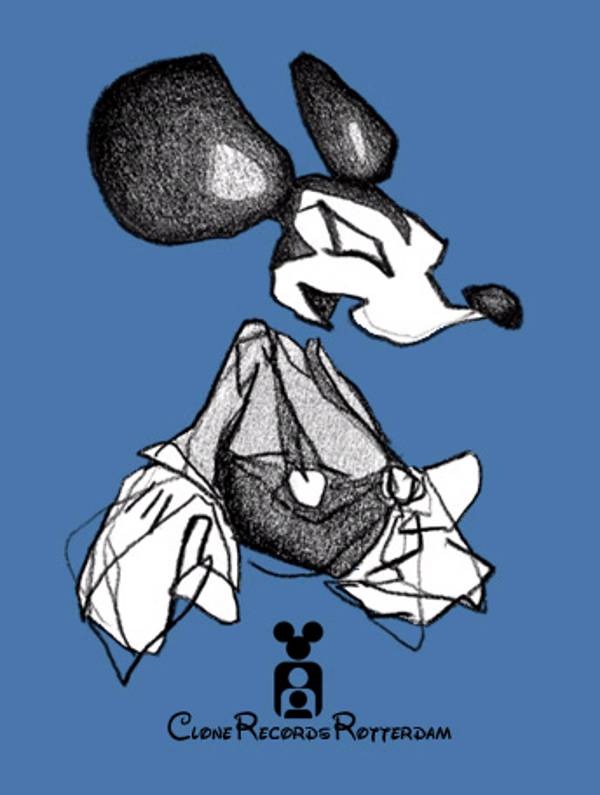
-你相信對於現在的音樂產業來說,還需要唱片公司的存在嗎?
Serge: 是的,當然有需要。
完全的無政府主義聽起來很理想,但這實際上是與藝術家和製作人合作的過程。
良好的合作能夠充分發揮藝術家和唱片公司的優勢。
這就像一份報紙──如果沒有一個好的編輯,一份報紙就毫無價值。
再看看 Spotify:每天有 10萬首新曲,這其中有多少是樹上的葉子,會隨著季節的變化而被遺忘?
每個月在 Spotify 數百萬首歌曲中找到出色的新藝術家,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。
主流唱片公司有他們購買曝光度的方法,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穩固網絡的獨立唱片公司,將好音樂帶給大眾。
當你喜歡並敬佩的唱片公司推出新唱片時,這就是對這張唱片的認可之處。
-你如何為 Carhartt WIP Radio show 挑選音樂?
Serge: 我希望保持混音的活力和實感,所以我挑選了很多過去一年中我一直在播放的曲子。
我還想給它一些獨特的元素,所以我選擇了一些有著與 Carhartt WIP 相同根源的曲子──來自底特律都會區的曲子,這是電子音樂的故鄉。
因此,這有點是一種致敬,因為混音中的大多數曲子都受到底特律音樂的影響,或者實際上是在那裡製作的。
-最近你都在聽什麼?
Serge: 我在家的時候聽來自世界各地的音樂。爪哇、峇里、日本、阿富汗和西藏的音樂,還有一些古典音樂。
當然,我大部分時間都在聽新的舞曲音樂,但我從不在家裡播放這種音樂。
寧靜的聲音,對於我的耳朵來說,通常是一種享受。
-你自身目前有正在製作中,準備發行的作品嗎?
Serge: 目前,我正在和我的朋友 Alden Tyrell 一起製作一些混音。
即將推出的混音專輯,包括 The Exaltics 的混音,和我們為 Frequency(又名Orlando Voorn)剛剛發布的混音。
我們還為 John Daly 製作了一張 house 混音,將於下個月推出。
-你是個狂熱的自行車愛好者。這份熱情有透過任何形式,連結你對音樂的喜愛嗎?
Serge: 再次提到了身體活動!我想這就是與音樂的聯繫。
我喜歡參加運動,這是我一直以來都在做的事情。我從十幾歲就開始衝浪,單車也是一樣。
我喜歡冬天的越野單車,夏天參加一些當地的比賽;騎著山地車出去玩,穿越單車道,或者和朋友一起在公路上騎行。
這能讓思緒清晰,而且很有趣,但這也是我唯一喜歡觀看的運動。
比賽結束後總是有很多故事和長時間的分析,它擁有許多小的內幕細節和團隊戰術。這就像下棋,但同時要把身體推向極限。
當然,Kraftwerk 也表現出他們對這項運動的熱愛,所以這種聯繫將永遠存在。
-有沒有一些事情是你一直都很想去做,但還沒能夠達成的?
Serge: 我仍然希望能在加州進行一次自駕旅遊,帶著我的衝浪板沿著海岸旅行。
我只在短途旅行中參觀過那裡,並沒有參與衝浪,所以我需要盡快實現這個夢想!
-作為居住在鹿特丹的人,你有什麼地方或秘境可以推薦給來訪的人?
Serge: 到 Demon Fuzz 進行一些唱片挖掘(當然還有 Clone.nl 商店),或者參觀博伊曼斯博物館,那裡有一個可愛的藏品。
他們目前正在翻新博物館,但他們的藝術品存儲倉庫也很不錯。
可以去 Woei 的運動鞋店,或者租輛自行車,發現南區的卡滕德雷赫特和 Kop Van Zuid 。
然後在唐人街,Kruiskade 附近的 De Toko 用餐或午餐,那裡的煎餅或雞肉炒飯,是我一些美國朋友的最愛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