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2021年底推出的 Hollow Earth Transmission(HET)是一個出版物和短暫物品(ephemera , 存在時間極短之物品或生物)的檔案室,特別關注於網路時代之前的文化。
主要出現於 Instagram 上,HET 旨在記錄印刷品在塑造我們集體意識方面的影響,涵蓋的主題從英國 1960 年代的左翼異議份子、到被禁的日本文學雜誌。
每篇貼文的核心思想是,印刷是一種具有顛覆性能力的媒介,能夠逃避審查,運作在權力和權威的視線之下,或許帶有一些諷刺的成分。
這種精神不僅塑造了 HET 上的許多存檔出版物,同時也喚起了早期網路的精神 —— 一個尚未被明確定義的空間,人們在其中尋找反映他們特定洗好和潛在身份的社群。
這是一個與我們今天認識和互動的網路世界截然不同的空間;它的強大潛力早已被廣告和多巴胺誘發的通知淹沒。
在最新一期的WIP雜誌,我們邀請 HET 背後的視覺藝術家 Niall Greaves ,創建一本向網路時代之前的印刷品致敬的出版物,並由作家和藝術家 Brad Phillips 附上一篇散文,懷念 Internet 1.0 的古怪和詭異之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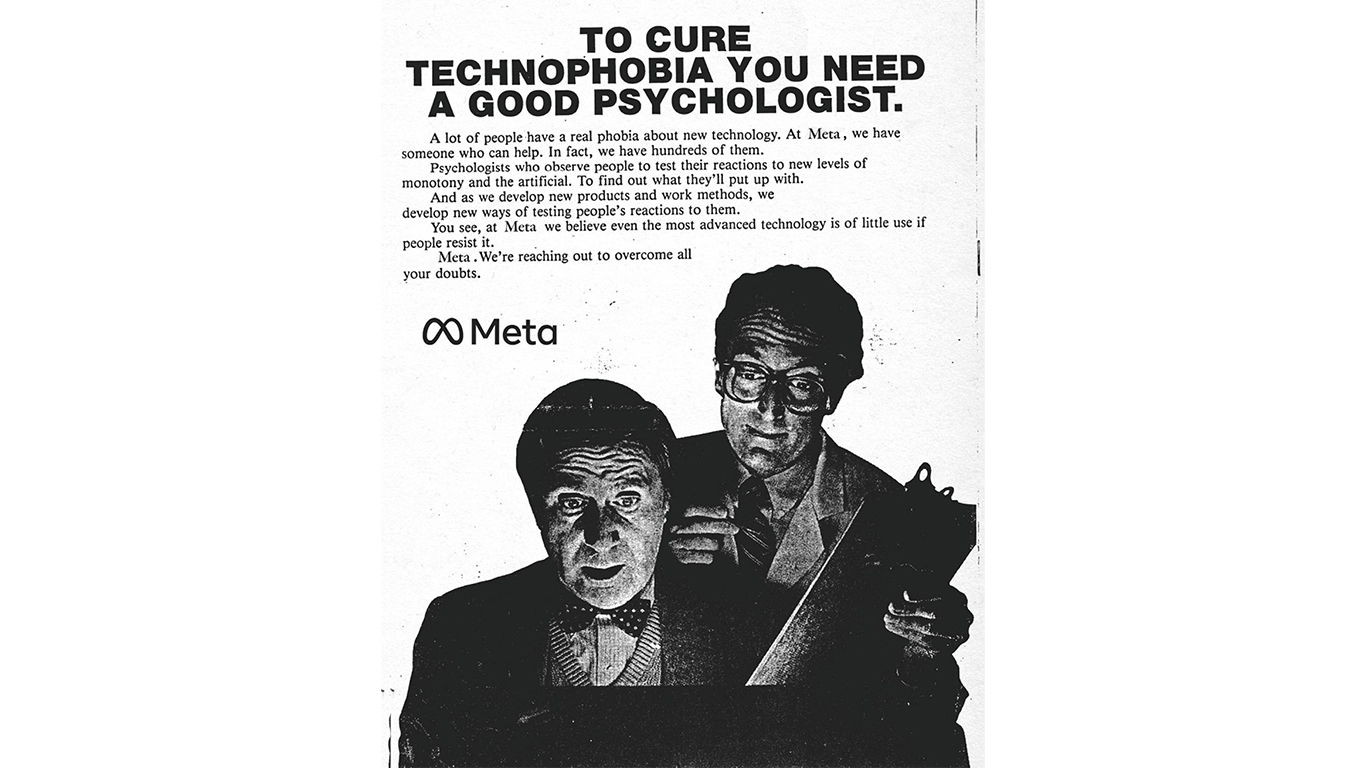
Internet Before Christ Words by Brad Phillips Artworks by Niall Greaves
Tony Soprano 曾經把“記得當時”形容為最低級的談話方式,而我先前曾在出版物中聲稱“沒有什麼比懷舊更痛苦”。
但在談論早期網路時,無論是“記得當時”還是沉浸在懷舊情懷中都是無法避免的。
因此,如果這篇文章背離了我的信仰並證明了 Tony Soprano 的觀點,請歸咎於網路,而不是我。
我在 1990 年 上線。,那時我十六歲。
我的第一個數據機是我第二表兄 Ronald 送的,他是我 WASP(白人安立奎人、蘇格蘭愛爾蘭人)家族中的一個異數,他巧妙地類比了 1991 年與當今的網路。
Ronald 是一位裸體主義者,有傳聞說他和妻子是 swingers 。
裸體主義者和 swingers 都是正常社會中的禁忌教派,他們試圖在壓抑的道德結構中最大程度地追求快樂和個人自由。
早期網路對於像Ronald這樣的人來說是一大利好,使他能夠與世界各地的其他志同道合的自由主義者交流。
那時的網路,就像交換伴侶一樣,是神秘而專業化的。有秘密代碼、規則和禮儀。
而且,就像在克利夫蘭郊區的假日酒店舉辦的某個交換伴侶週末一樣,最重要的是匿名性。
第一批會去應對新發明的人通常是最需要它們的人。
要解碼和使用任何事物的早期版本,你首先必須感受到對它的需求。
1991 年的網路主要由公告板組成,是報紙和雜誌的數字版本。
除了科技愛好者之外,任何擁有特定興趣的人,就像我表兄 Ronald 一樣,立即會抓住這些網站所提供的匿名性和功能。
在九十年代初,網路是你必須尋找的東西,過程中會伴隨著各種困難。
能夠上線的人,很可能是學校或社區中僅有的少數。
你可能在上歷史課的路上碰到另一個有數據機的人,而你們兩個都不會知道你們分享著這個秘密生活。
也許他們將時間花在龍與地下城的公告板,而你則在《星際迷航》、食譜或 NASCAR 的公告板上度過你的夜晚。
到了 2023 年,每個人都在線上,被要求上線,而我和許多人現在尋找的是一種離線的方式,這感覺比 90 年代的情況要困難得多。
所有美好的事物終究會結束,而當它們在我們這個時代結束時,通常是因為企業的貪婪和對個人自由的日益壓制。
那麼,我很久以前在線上做了什麼,我喜歡什麼?如果早期網路所代表的自由已經消失,那就讓我來致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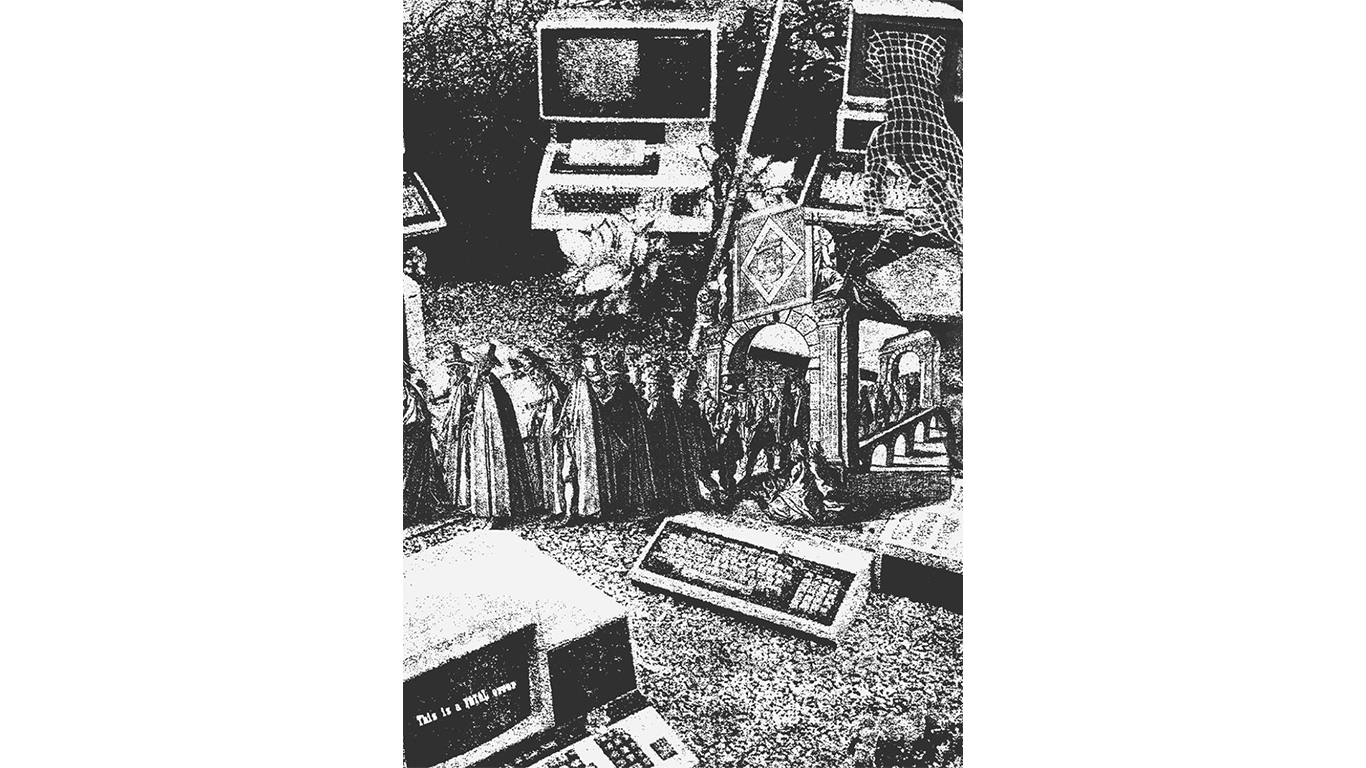
1.
在我高中時,我確實在走廊上遇到過其他也在線上的人,而我並不知道。
1991 年,我加入了一個以 Pyroto Mountain 運作的公告板系統。
維基百科將 Pyroto Mountain 描述為“基於回答問題和技能測試問題的在線遊戲”。
我幾乎記不得當時的細節,但記得我的數據機需要將近一分鐘的時間來連接,而這段時間我的臥室聽起來像是兩隻黑猩猩在拼命搏鬥。
那裡有基本的圖形,模糊的目標,而且沒有廣告。不可能與其他玩家實時聊天,但我們可以在留言板上發文然後返回查看回應。
Milky Puppy(以下簡稱 MP )是一個在該站活躍的人,所使用的名稱。
終於,我意識到 MP 是我的同學。他提到了一本叫做 Yip 的小冊子,我在午餐時見過它被傳遞。
我開始在 Pyroto Mountain 上給 MP 留言,而也會收到他的回應,他成為了我在網路上的第一個朋友。
在12年級快結束的那天,我在圖書館看到有人在用影印機複印 Yip ,那就是 MP ,而那一刻感覺有點尷尬。
在線上,我們都自信而諷刺。現實中,我們都安靜、缺乏安全感且像書呆子。
我不能分享他的名字,但我們的友誼持續發展,以至於在 2001 年,當他接到醫院打來的電話說有一個肝臟可以進行移植,他應該儘速前往時,我正在和他的女朋友以及當時的妻子一起吃晚餐。
在知道彼此身份後,MP 和我並沒有開始在學校一起玩。
相反,他與我分享了其他網站,其他公告板系統,透過他我認識了更多人,其中很多人住在我小鎮上。
在我二十出頭的時候,每週我們都會在當地的酒吧聚會,參加智力問答夜。
一群在線上互動的人一起喝啤酒,充分發揮自己的怪癖知識。
在那些年裡,MP 創辦了自己的網站 Infiltration.org 。
他是現在被稱為都市探險(Urbex)的先驅之一,這是一種闖入受限制的公共空間,唯一目的是探險、攝影,並留下零痕跡的行為。
他的網站至今仍然存在,還有一本書,他在這個社群中是一個傳奇。
就像表兄 Ronald 一樣,網路對於 MP 所在的這個世界的人來說,是一個理想的地方。
由於他們在追求愛好時會觸犯眾多法律,必須保持匿名性,以便發布照片並分享信息。
如果不是最初的 Pyroto Mountain ,我永遠不會知道都市探險,也不會尊重它,並成為MP的朋友。
整個次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多倫多郊區的一位書呆子催生的,對名聲或利潤不感興趣,這種態度在2023年大多數在線追求中似乎是相反的。
2.
MP 跟我分享的其中一個網站,同樣也是公告板,名為 Powderkeg 。
像大多數傾向於憂鬱的書呆子一樣,我有時會寫詩,而 Powderkeg 嚴格來說是一個詩歌板。
同樣,沒有聊天,沒有廣告,也沒有金錢。
我的詩歌很糟糕,但在 1993 年的某天,有人在我發布的一首詩歌下留下了一條鼓勵的評論。
他給我發了一條私人訊息。Ian 是多倫多大學的英語文學專業學生,這正是我想去的地方。
我們交換了 email 。
有一天我鼓起勇氣,和他約在市區見面。(我沒有父親或兄弟,一直都容易被父親般的關注吸引。)
那年的 Lollapalooza 2 在多倫多市外舉行。我沒有車也沒有駕照,但我有一個想去的女朋友。
音樂節前一天晚上,Harmony 和我坐火車到多倫多,在 Ian 和他的女友家住宿。
對我來說,這是異國情調,幾乎有些危險。Ian 和他的女友和我們一起抽了大麻,儘管他們才二十多歲,但似乎更像五十歲。
我立即感覺自己像個成年人。
早上我們早早醒來,擠進他的車,開了兩個小時到達音樂節場地。
我在中暑之前看到了 Ministry ,Cypress Hill 和 The Jesus and Mary Chain 。
幾小時後,Ian 和 Harmony 找到我,我躺在車下。
我們開車返回多倫多,在接下來的幾年裡,我偶爾和他以及其他新手詩人見面喝咖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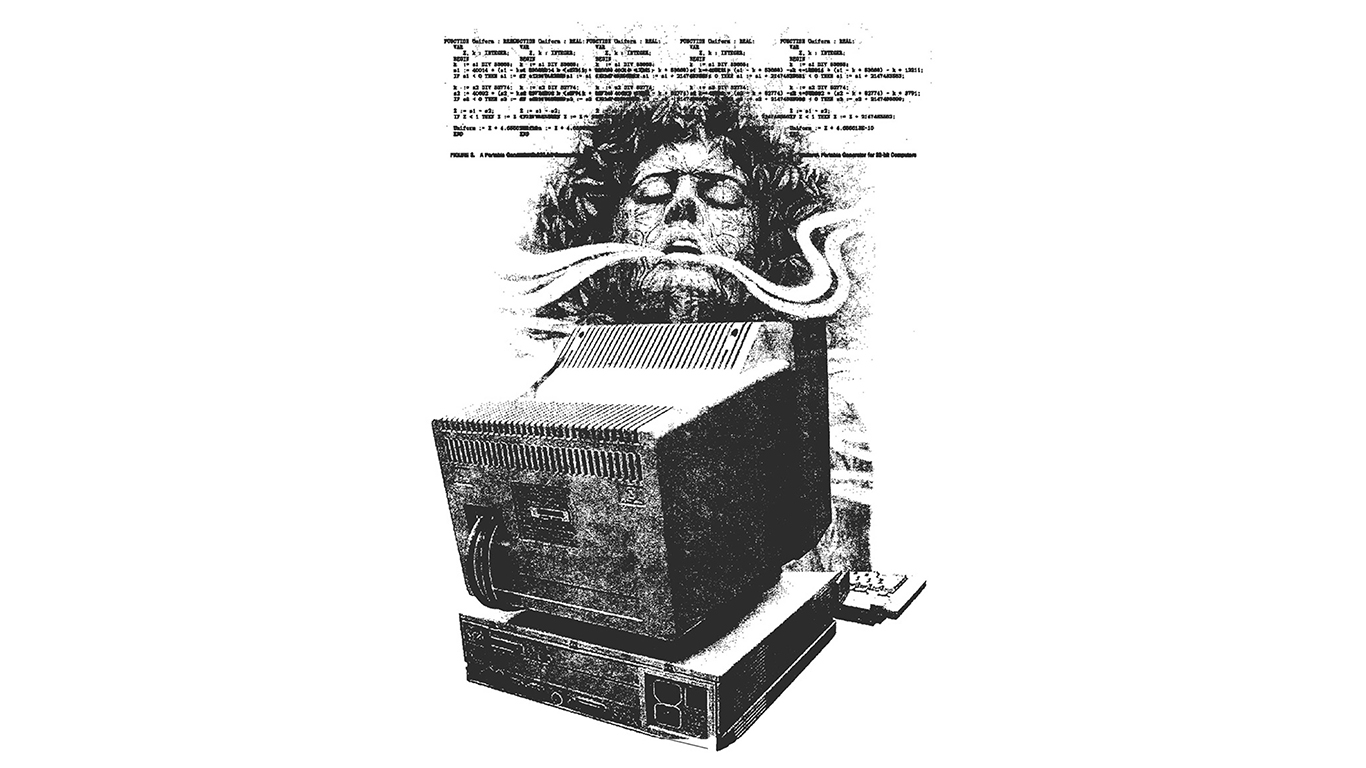
3.
從 1993 年到 2013 年,我與網路的連結幾乎完全圍繞著一個名為 ISC.RO 的網站,即網路 Scrabble 俱樂部。
在我成長的過程中,我和我的祖母一起玩 Scrabble ,她早早地灌輸給我對詞語和書籍的愛。
在某個時候,我比我的祖母更強,開始故意輸掉比賽——她是一個極度不善輸的人。
ISC 由羅馬尼亞託管,是唯一不會受到 Scrabble 原始制造商 Parker Brothers 訴訟的 Scrabble 網站。
作為一個喜歡獨處和大麻的人,線上 Scrabble 讓我能夠集中精力並同時避免生活。
我在這個網站上變得非常有名,既因為我不停的嘴硬,又因為我在三分鐘的比賽中能夠打敗大多數玩家。
在那段時間裡,有時我一天會玩超過一百場遊戲。我很久沒有在那裡玩了,但剛剛登錄查看了我的統計數據。
WINS: 34616
LOSSES: 19951
DRAWS: 470
這種程度的 Scrabble 類似於交換伴侶和裸體主義。
它充滿了秘密語言,特定的禮儀,正如我對交換伴侶和裸體主義的經驗一樣,它主要由書呆子組成。
ISC 也讓人聯想到早期的網路:圖形很差,因為它們不需要其他形式、沒有廣告,也沒有需要購買的東西。
我和 NoChance4U(佛羅里達州蓋恩斯維爾的一名牙醫)、ikantspell(貝爾法斯特的單親母親)以及 giJoel(GI Joel Sherman,因為他有著腸胃問題並經常飲用 Maalox ,他是 Scrabble 紀錄片《Word Wars》的主演,1997 年世界 Scrabble 冠軍,也是紐約市北美 Scrabble 玩家協會俱樂部 #56 的負責人)等人一起玩遊戲。在我下週四要參加的比賽中,他擔任指導員。
在 ISC 的這二十年中,我經常在腦海中進行單詞的字母重新排列,而且這不是我主動進行的。
我玩得如此之多,以至於改變了我的大腦結構,讓它成為一個追求最大分數的字母重新排列機器。
二十年前,如果有人告訴我我會和 Joel Sherman 一起在同一個房間裡玩 Scrabble ,他是有史以來最著名的 Scrabble 玩家,我肯定會說這是胡說八道。
但是下週四,我和妻子克里斯汀將參加紐約俱樂部的第一次見面會。
這是一種與特定社群相連結的方式,這正是 1990 年網路的目的,也可以說是網路的創造者所期望的。
十五年前,我在溫哥華的一個房子裡看著《Word Wars》,看著喬爾·謝爾曼流汗、吃胃藥,然後出現了兩百多分的單詞。
下週四,我將親自見到這一幕。
這是花時間尋找而沒有特定目的的成果,通過探索學習我感興趣的事物,然後加以發展。
我不需要算法或定向廣告來達到這一點,我需要擺脫這些事物的束縛,以及對好奇心的允許。
在我這個年齡,四十九歲,重要的是不要聽起來像一個守舊的老人,不要帶有價值判斷,也不要沉溺於懷舊之情,但我對即將到來的世代感到真正的擔憂,他們將被引導去追求市場預測他們會喜歡的東西,始終在追求他們的金錢和注意力。
我很高興我在那個時代上線。在 1991 年,我是那個手握方向盤,將這個混亂的發明帶到我想要去的地方,探索文化的新領域和自己的思想。如今,網路被宣傳為個人自由的工具,但它是一輛自動駕駛車,確切地知道它即將帶你去的地方,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。
如果你不喜歡,你會學會接受。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你被引導遠離其他部分。